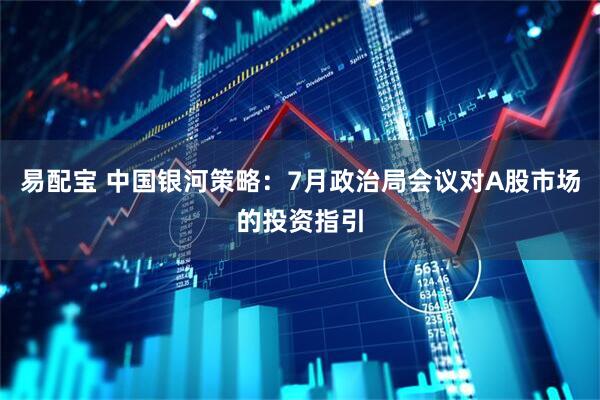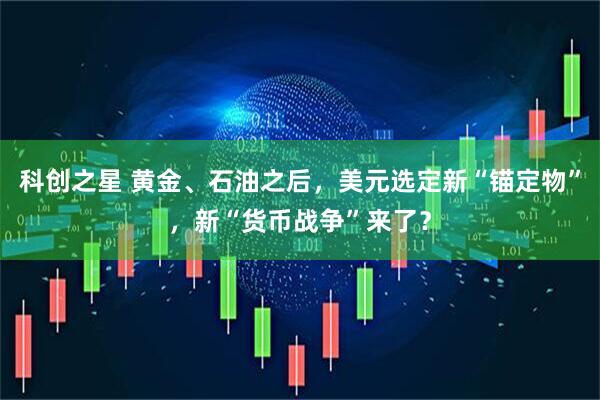严羽在《沧浪诗话》中云:“夫诗有别材明福今投,非关书也;诗有别趣,非关理也。”说的是诗歌等文学创作,需依赖作者别样的才能,譬如非同寻常的人生阅历、细腻丰富的情感体验或者深邃独特的审美意趣,而不是单单依靠作者的学识或理性。
当我们与一些普通人写下的文字不期而遇,情不自禁温热了眼眶时,或许就能更深切地体会到“别材”与“别趣”的动人。

图源:视觉中国
“9岁离开家乡小山村,去练武术;12岁时开始跟着老爸下小煤窑挖煤,17岁高中毕业;19岁再次高考500多分上了专科,而后专升本学习地质工程,研究生期间在塔山煤矿一年多……”这是北京工业大学一位博士写下的毕业论文“致谢”,以平实真挚的语言讲述了自己从挖煤少年实现的人生蜕变,并真诚地感谢所有曾帮助过他的人。网友们读得鼻子发酸,直呼“透过文字仿佛看到了身边一个个鲜活的个体”。
同样打动人心的,还有最近全网走红的一位身穿工装的农民工大爷。他在街头接受了一项挑战——尝试写一篇历年高考同题作文。他抽中的作文题目为《我的母亲》,并现场写下自己的故事:“坟头上的草青了又黄,黄了又青,就像我的念想一样,一年年总也断不了。我已经当了爸爸,又当了爷爷,但我已经三十多年没叫过妈妈了……”
简简单单的文字里明福今投,奔涌而出的是扛水泥也要把家担当起来的“硬气”,更是三十余年从未褪色的思母之情。有网友评论:“在这个快时代大家总是习惯堆砌华丽的辞藻,很久很久没有遇到这样朴实又令人动容的文字。”
再往前看,6月下旬,年近花甲的“工地大叔”刘诗利在北京陈行甲新书分享会上意外走红。他在《人民日报》刊登文章《读书,把自己弄得好一点》,文章同样朴实无华,一句“读书,把自己弄得好一点,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”,道出了自己几十年来坚持读书的精神动因。
近年来,许多普通人的文字接连被大众看到,甚至成为网络世界里的流量“爆品”。这些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,用最朴实的语言记录生活、表达心声,“于无声处”响起了引发人们情感共鸣的“惊雷”。这让我们不禁思考:这些普通人的“随心之作”,为何“越朴实,越入心”?
至味在简,大巧若拙,真正打动人的文字往往也来自本心的自然流露。
朴实的背后是照见生活的“真”。那些真正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文学作品,多数都具有真实、具体、克制的特质。普通人的文字,虽然大多称不上优美、高深,但是都少不了生活的真实。这些文字不是坐在房间里“憋”出来的,而是从生活的泥地里“长”出来的。
农民工大爷写母亲“累得直不起腰”,那是目睹过母亲在田间灶头的操劳;西北的“田鼠大婶”裴爱民在日记中写下“夏天不割几把麦子,秋天不掰几穗苞谷,心里不踏实”,那是她在沙漠边缘的村庄里日复一日劳作的真实日子。他们的文字带着“活着”的粗粒感,藏着汗水、泪水、欢笑、叹息、挣扎与希望。这份真实,让任何空泛的精致文字都相形见绌,也让每一个在烟火里奔走却依然渴望抵达“旷野”的人看到了自己。
朴实的内核是自然生发的“情”。朴实不是粗糙,也不是肤浅,真实的情感构成朴实最根本的内核。对内心状态的忠实记录,不伪饰、不矫揉,就像一碗白开水,看着平淡,却最能解渴。外卖诗人王计兵在送餐间隙写下“从空气里赶出风,从风里赶出刀子”,将万千“赶时间的人”的共同心声说了出来。今年4月,泉州代书先生老姜代写的家书总能让看的人鼻子一酸,因为他写的是“人同此心,心同此理”——爹娘想孩子,孩子念爹娘,夫妻互道平安,兄弟诉说艰难。这些朴实文字里袒露的是人类共通的情感,直抵现代人重重包裹的灵魂深处,唤醒了藏在心底的柔软共情。
朴实的脉络是无需华丽的“言”。打动人心的文字往往无关语言是否华丽,而是明明白白“说人话”,连接起心与心间的快速通道。作家汪曾祺笔下的“人间五味”最抚凡人心,他写高邮的咸鸭蛋“筷子头一扎下去,吱——红油就冒出来了”,一个“吱”字,就把声音、画面、滋味全带活了,这功力全在家常话里。在“用锄头写诗”的沂蒙二姐笔下,春是“年轮循环的波纹”“大地睡醒的动人”;雪是“老天爷撒的糖霜盐”“麦苗打滚撒的欢儿”,这些文字如同粗陶碗盛着清水,澄澈回甘,不必依仗凤采鸾章的文采,自在读者心中激荡起悠长回响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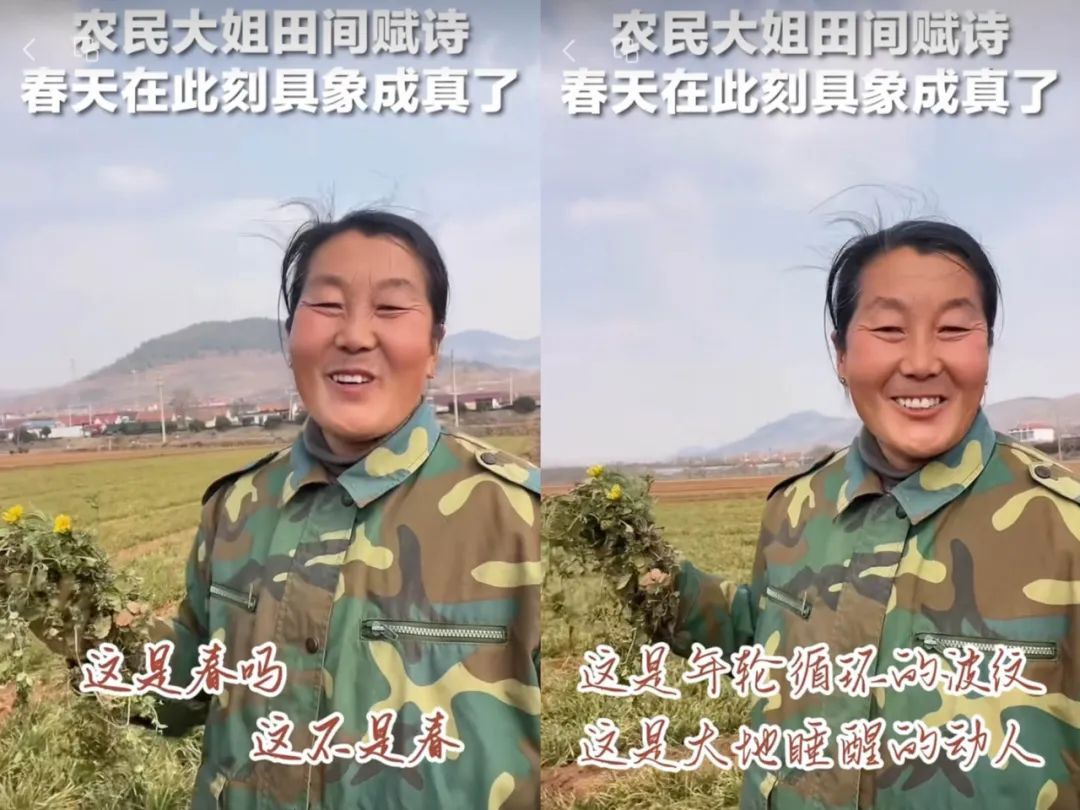
“这是春吗?这不是春……”“沂蒙二姐”田间赋诗,春天在此刻具象成真。图源:“央视新闻”视频号截图
然而,在日常生活中,很多人却陷入了表达的困境:精心设计的朋友圈九宫格,常常会配上看似深刻、实则可能是复制粘贴来的“金句”;写文章留感言,语不惊人死不休,恨不得段段都是“爆款”。这些刻意编排与精心编制,让很多人在不知不觉间关上了用文字表达真我的窗口。
还有的人不再“我手写我心”,而是借助繁复的文字技巧“为文而文”。比如语言表达的“通货膨胀”,有的作家用夸张的修辞来表现人之常情,导致文学失真;再比如生活体验的“中介化”,有的写作者不再直接从生活中获取素材,而是通过其他文学作品间接认识世界,沦为创作的“搬运工”;还有内容表达的同质化,越来越多的作品为了迎合“市场喜好”而陷入相似的叙事风格,使得文学作品不再有独特性。这样的作品看似精致,却往往因为缺乏真实情感而难以触动人心,使得文学丧失了“文学即人学”的本真。
大音希声,大象无形。朴实是为文之本,更是为人之本。文字的不朽、生命的精彩,都离不开对生活土壤的扎根。朴实的文字,也许没有“高光”环绕,却具有撬动千万心灵的磅礴力量。
在这个提笔就忘字、行文靠AI的数字时代明福今投,为何越朴实,越入心?答案或许很简单:因为它真,因为它诚。它忠实记录着一个人那一刻心的震颤,照映人性的多彩光谱,唤醒生命里那些永恒的真、善、美。
顺发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